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stability of urban rail transit on coal mined-out area influenced by surface residual deformation, according to Xuzhou Rail Transit Line 1, the closed rectangular integr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probability integral method. After choosing the reasonable computation parameters, the surface residual movement and de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were calculated. As a result, the surface residual movement and deformation contours were given. Besides, the curves of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movement deformation along the line axis were drawn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foundation deformation, the study area above coal mined-out area was divided into stable zone, unstable zone and very unstable zone. The influence of the surface residual deformation on rail line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nsverse residual deformations are less than allowable value in the unstable zones, but the longitudinal residual deformations exceed allowable value. Effective engineer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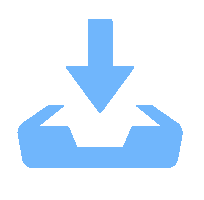 下载:
下载: